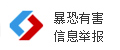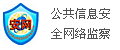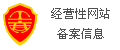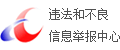|
译者赵玉皎在日本长野县安昙野,这里是宫崎骏电影《起风了》的背景风光。
济南时报·新黄河客户端记者(以下简称记者):目前磨铁图书已经出版了两本简体中文版的宫崎骏作品,分别是《龙猫》与《千与千寻》,这两本绘本均是您担任翻译。可否谈谈翻译宫崎骏作品的始末?
赵玉皎:吉卜力工作室还是首次对我国大陆地区授权出版宫崎骏绘本的简体中文版,磨铁有狐在众多竞争者中胜出,获得了吉卜力工作室的认可。除了刚出版的这本《千与千寻》与2020年末的《龙猫》之外,接下来还会有其他作品陆续与读者见面。
在磨铁有狐获得授权后,我接到了翻译邀约。我从青年时代起就是宫崎骏的忠诚粉丝,能够在多年后有幸成为这一系列作品译者,感到非常惊喜,有种旧梦重温之感。由于译者需要吉卜力工作室进行确认,我提交了日文履历书,并作了试译。得到认可后,我在2020年2月着手翻译《千与千寻》,由于故事本身非常紧凑流畅,译稿也有点“一挥而就”的意思。不过后期的修改润色过程非常漫长,我们建了文字编修群,大家反复核对电影画面、电影对白和台版书,每个细节都一遍遍地进行推敲,才有了最终的文字稿。
记者:翻译这本《千与千寻》,与翻译其他作品有何不同的感受?
赵玉皎:有的。在我多年的翻译工作中,宫崎骏系列绘本是非常特殊的存在,因为它来自于动画电影,是将流动的电影画面定格化加以留存的作品,而不是依靠文字来建构一个想象中的世界的狭义的文学作品。
电影中,由于富有张力的故事情节、细腻的画面和富于感染力的音乐,能够向观众鲜明而强烈地传递出作品的气氛和风格。定格后的绘本,文字成为画面的辅助,替代了电影中的对白和音乐,但向读者所传
递的气息与电影的氛围是一致的。因此,电影绘本的文字没有、也不应当有太大的自由度,作为译者一定要清晰自己的定位。也就是说,当翻译传统文学名著时,译者可说是“作者与读者的桥梁”,有较强的译者主体性;但翻译《千与千寻》这样的电影绘本时,译者更像是产品制作团队中的一员,重心在于恪尽职责,将电影中的原对白译文、流传已久的专有称谓、版权方的要求、编辑团队的意见进行融合,在完成这些功能性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追求美感。有句玩笑话说,“翻译好比戴着镣铐跳舞”,从自由度的角度而言,《千与千寻》的翻译可说颇有点这个意思。希望这些配在画面旁边的文字,能够对得住原作中的文笔,不至于减损画面的美感。
记者:您如何评价宫崎骏的电影与文字风格?
赵玉皎:宫崎骏的电影数十年来长盛不衰,一代代少年和青年痴迷他的作品,人到中年回头重看,又会有不同的感慨涌上心头。这种神奇的没有“年代感”的特性,大概是由于宫崎骏作品内涵的广阔性和层次的丰富性决定的吧。
宫崎骏喜欢探讨较为永恒的主题,关于自我的迷失与找寻、关于生命的实现、关于人与自然的共生、关于爱、关于人性等,即便作品背景有确切的年代,依然可以穿越时间,引发我们的共鸣。他的作品又有一种奇妙的普适性,处在不同的年龄段,我们可以获得不同的感动,随着知识和阅历的增长,对同一作品的理解也会不断加深。此外,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宫崎骏作品有一种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洋、奇幻与真实相交融的美感,孩童们可以看到蓝天、绿草和龙猫,成年人可以看到宫泽贤治的列车、夏目漱石的山崖和《奥菲利亚》油画,每一部作品都像一个藏着无数惊喜的宝藏。
宫崎骏的绘本是电影的伴生作品,要用有限的画面完成故事的叙述,那么文字势必要承担情节推动的功能,不可能用太多文字来进行细腻的心理或景物描写。所以在绘本中,宫崎骏本人的文字也不太可能有很大自由度,只能用简洁的文字来有效地描述情节。但尽管如此,与电影整体的氛围相协调,宫崎骏文字还是非常优美生动。
记者:您之前的儿童文学译本《窗边的小豆豆》广受好评,这次作为宫崎骏系列绘本作品的译者,也受到了吉卜力工作室、磨铁图书以及读者的认可。翻译好儿童文学作品,除了较高的日语素养之外,您认为更重要的是什么?
赵玉皎:儿童文学作品的外语读解难度并不大,我的学生们在本科二年级的时候就可以试着翻译一些童话了,但译文的差距非常大,有的很平板干涩,有的就显得灵动润泽。
我想,翻译好儿童文学作品,最重要的可能有两点,一是觉得“有趣”,二是觉得“有意义”。
“有趣”就是译者本人的性情与儿童文学天然相近,最好是童心未泯,至少也要能够共情。其实想一想,那些动人的优秀童话,绝非是孩子们的专有品,而是人类描绘出的最美的梦境、最理想的世界和对自身最深切的反思。
“有意义”是译者能够从翻译儿童文学作品中获得足够的价值感。目前文学翻译的现状,基本还处于靠“爱”发电的阶段,儿童文学翻译尤其常被认为很简单,在社会认可度和学界评价中,远不如经典文学翻译受到尊重。因此,译者自身能够认同这种工作的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正如儿童食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样,孩子们的精神食粮也必须是健康而富有营养的,参与优秀作品的制作,精心打磨出优美的、流畅的、富于节奏感的文字,为孩子们的成长尽一份绵薄之力,正是这份劳作的价值所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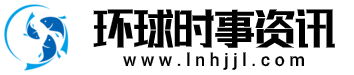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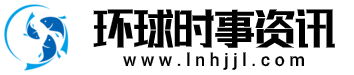
 主页 > 娱乐 >
主页 > 娱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