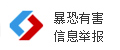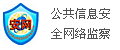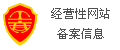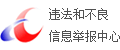|
诺兰新片《信条》甫一上映,观众口碑就呈现出两极分化。但无论表示因为喜欢而选择二刷三刷的铁粉,还是电影没结束就愤而离场的观众,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这部片子不太好懂。
不太好懂几乎已成为诺兰电影的标识。这些表面上看起来不太好懂、对观众不友好,但实际是对观众发出强烈召唤,需要观众与电影一起玩游戏的电影,被电影理论家埃尔塞瑟形象地称为心智游戏电影。这些影片里常常会有诡异的细节、复杂的叙事、心智失常的主人公等,让观影过程变得十分烧脑,甚至必须多次观看,才能对影片完全掌握。
从2000年的《记忆碎片》开始,诺兰的电影大都可以归入这类心智游戏电影之中,或至少具有心智游戏电影的某些元素。而且诺兰的厉害之处是能够将心智游戏作为新配方加入商业大片之中,从独立导演起步到成为如今商业大片数一数二的导演,并且逐渐改变了大片的特质,让其不再仅仅是华丽的大场面,也不仅仅只是流畅叙事加个性人物,它还可以、也必须加入更多新的时代内容。
信息量超载的谜题:多平台与召唤粉丝
1980年代之后的电影工业几乎可以被称为商业大片时代。作为高投入、高科技、高风险的生产,大片也推动着全球电影工业走向跨媒介的水平联合体新生产机制。票房不再是大片的主要收入,电影的经营活动越来越多地与其它行业交织在一起,比如电视、游戏,甚至玩具、主题公园和食品业等等。但大片内容如何承担起这种多媒介的新生产机制则存在很多讨论的空间。当大众渐渐对故事简单、充满视听盛宴的高概念大片产生审美疲劳的时候,诺兰从心智游戏电影那里找到了一种新玩法——信息量超载的猜谜游戏。
心智游戏电影就是一种十分适应多平台,为观众多次观看设计出来的电影。首先可以用其特效和奇观价值去吸引进影院观影的公众,再通过成为信息交换素材和网络的冷知识和秘闻来吸引网络上的粉丝社群,还可以进一步促成DVD、游戏及其他衍生品等的发行。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心智游戏电影中所提供的信息量往往比一般的电影多得多,因为这些电影制作出来就是为了鼓励重复性的观看和吸引狂热的粉丝。这些粉丝接下来会在网上建立活跃的粉丝基地来与电影进行互动。
很多心智游戏电影导演也会非常鼓励粉丝对电影的猜谜行为,比如诺兰就是一个积极鼓励粉丝互动的导演,不仅擅长在电影中设置各种“锁眼装置”,而且通过各种宣传指导观众投入到这个解锁游戏之中,达到吸引大量观众进入影片的目标。在《信条》中,诺兰依然投放了大量召唤粉丝的“锁眼装置”,比如网上已经展开热烈讨论的TENET的涵义、无名的主角、熵、祖父悖论等等。这些饵料诱使粉丝积极进入对电影文本的讨论,并狂热地一遍遍回看影片,也为影片进一步在不同平台扩展故事世界奠定了基础。从《信条》所留下的大量空白来看,制片方甚至可能已经考虑了续集的拍摄。这种种手段,都与目前多媒介的新生产机制密切相关,揭示着商业大片的内容和架构在新生产机制下的悄然变化。
复杂叙事和心智异常主人公:科技强势时代的感官训练
除了信息量超载和大量谜题,心智游戏电影另外的显著特征就是叙事的复杂和主人公的异常心智。这些特征与我们目前的科技强势时代密切相关。
以叙事来说,在计算机和因特网驱动下,人们需要更多动态的、实时的反馈和反映,而且连结网络的热点和节点也明显地与线性思维分道扬镳。因此,心智游戏电影可以看作是“书写系统在广泛监控、实时性和永恒反馈等条件下的叙事”。而那些受到良好教育的网民以惊人的速度适应了这种体系背后的迷宫通道和导航原则,对一些新的复杂叙事有着天然的需求和亲近感。诺兰所获得的非线性叙事大师、后现代叙述大师等赞誉与他在电影中不断探索复杂叙事的可能性密切相关,也恰好满足了这些新观众对复杂叙事的强烈渴望。
心智游戏电影还十分喜欢塑造心智异常的主人公。在诺兰的成名作《记忆碎片》中,主人公就患有失忆症。还有诸如精神分裂症、妄想狂、歇斯底里症等都是心智游戏电影十分喜爱的主人公状态。这些病症性人物看似失去了控制,但他们的思想却有可能获得一种与我们目前所处的人造的、程序化的和自动化的环境的新关系,成为适应这个由媒介与科技统治环境的新人形象。比如妄想症对我们现在所处的网络社会可能变成一种财富,它能够依靠身体直觉,对环境高度敏感,从而发现新的联系。《信条》里反复告诫我们不要试图去理解,而是去感受,就是一种妄想症的思维模式。而失忆症则使人具有一种随机反应、多重任务的人格特征。《信条》的主人公就被塑造成失忆症的状态,他虽然来自未来,但却对此毫无记忆。他的身体被完全编辑到这个拯救世界的程序之中,失忆反而成为一个武器,让他就像一个聪明的炮弹,不断接受被编程的任务并严格执行。
但《信条》的主人公设计确实有些太“机器”了,完全去除个人身份,连名字都没有,这可能是导致《信条》让很多观众无法与主人公形成共情,在观影中获得情感满足的重要原因,不像之前的《星际穿越》等都非常好地利用了情感力量来调剂心智游戏电影的前卫感。
未来焦虑:作为思想实验的大片
心智游戏电影还喜欢多重时间安排和前后移动的时间框架,而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对未来影响现在和过去可能性的思想实验。这种思想实验在被埃尔塞瑟称为心智游戏电影之父的美国科幻小说家菲利普·K·迪克的科幻小说中就反复出现,也被大部分的心智游戏电影所继承。这种循环时间的安排表征的实际上是一种现实的危机感和对未来的焦虑情绪,即通过焦虑地计算未来等待人类的风险,展示过去人类行为所形成的当下危机。
在诺兰的大片序列中,《星际穿越》就充满着这种对人类未来的焦虑,并巧妙设置了一个循环时间,将父亲的离去和归来重叠在一起。《信条》在未来焦虑的展现上更是淋漓尽致。影片以未来人类对现实人类发起攻击作为叙事的基本动因,因为现实人类的胡作非为,未来人类已经没有生存的空间,于是决定彻底毁灭现实人类。而影片的整体情节设计则是从现在回到过去的十分工整的循环拯救过程。《信条》中这种未来、现在和过去的复杂交织正是心智游戏电影未来焦虑思想实验的经典呈现。
值得注意的是,《信条》有意将本应成为主角的未来人类表现为不在场状态,也完全放弃了一般科幻片对未来景象的奇观展示。相反却采取了一种十分写实的影像呈现方式,甚至连本应充满科幻色彩的时间旋转门和时间逆流状态都太过真实,缺少视觉魅惑感。诺兰似乎想以这部“写实”影片真正警示人类,如果继续目前的状态,这样的未来并不是幻想。这种严峻的基调可能是《信条》作为商业大片另一个重大失误,将对未来焦虑的比重过于放大,加入过多的思想实验和反思内容,可能能够吸引一部分狂热粉丝,但会损失更大量的普通观众。因为当娱乐性和情感满足都无法获得,普通观众几乎找不到一个可以进入这部大片的入口,必然觉得沮丧。这也说明心智游戏电影的超载信息、复杂叙事和批判性反思对普通观众来说还是有不小的门槛,如果在商业大片中加入过多,可能会成为观影的阻碍。
但无论如何,诺兰还是实现了电影工业的新玩法。他之前已经成功的《盗梦空间》《星际穿越》《黑暗骑士》等大片,说明将心智游戏元素加入商业大片仍然是一种可行的新配方,不仅增加了大片的时代质感,能够对新的时代命题有更敏感的反应能力,而且也让其摆脱高概念大片的简单模式,让一些更复杂和有一定深度的内容能够进入大片之中。
诺兰的探索也说明,一些有探索精神的独立电影的存在完全可以作为商业电影的助推器,是应该受到电影工业重视的内容。而新一代观众对商业大片也有新的要求,他们渴望大片能够提供一些更让他们烧脑和惊叹的内容。这些对中国电影工业如何发展自己的商业大片是有启示作用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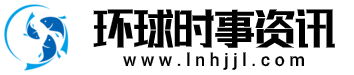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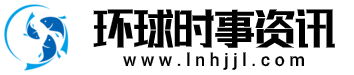
 主页 > 娱乐 >
主页 > 娱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