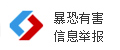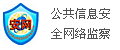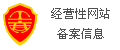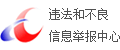|
202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三位研究人员。他们证实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可以预测黑洞,并确认银河系的中心是一个超大质量黑洞——体积相对虽小,但质量却相当于400万个太阳质量。超大质量黑洞周围的强大引力场,除了可以增加我们对黑洞的理解,也是我们在极端条件下研究自然的实验室。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来自UCLA的安德里亚·盖兹和其他研究人员,已经测量了强大引力是如何改变精细结构常数的。精细结构常数,是定义物理宇宙(以及宇宙中生命)的自然常数之一。这项研究也延伸了其他正在进行中的工作,从而去理解这些常数,以及去弄清楚它们是否会随时间和空间而改变。研究人员希望通过这些研究,找到基本粒子标准模型和当前宇宙学中种种问题的解决线索。 202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安德里亚·盖兹
和盖兹分享202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还有剑桥大学的罗杰·彭罗斯(他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黑洞的理论理解)和德国加尔兴马克斯·普朗克地外物理研究所的赖因哈德·根策尔。盖兹和根策尔展开了相似但独立的观察与分析研究,并各自推断出我们的银河系中心存在一个超大质量黑洞。从2.7万光年之外,获取高质量的数据需要使用大型望远镜。盖兹与夏威夷莫纳克亚山上的凯克天文台合作;而根策尔则使用了位于智利的甚大望远镜(VLT)。盖兹和根策尔都发现,他们观测到的恒星运动皆因银河系中心的巨大质量所致。他们也获得了相同的数据:差不多太阳系大小的区域,有着400万个太阳质量的质量。显然,这是一个超大质量黑洞。 盖兹在凯克天文台的研究也让她成为今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的共同作者。在这篇论文中,巴黎天文台的奥雷里昂·希斯和13位国际同事展示了银河系超大质量黑洞附近的精细结构常数结果。盖兹的研究,不仅摘得诺贝尔奖,也为该论文提供了数据支持。更值得注意的是,盖兹的研究在观察超大质量黑洞附近的恒星运动时,将当今理论和天文技术,与约翰内斯·开普勒和艾萨克·牛顿时期的思想相结合。这再一次佐证了牛顿在1675年,就科学发展表达的见解,他说:“如果说我看得比别人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就是这样一位巨人。他在1609年提出的行星运动定律改变了科学。他率先证明,行星并不是绕着太阳做完美的圆周运动。根据开普勒定律,行星沿椭圆轨道环绕太阳,而太阳则位于椭圆的一个焦点中。(椭圆有两个焦点,这两个点相对椭圆中心对称分布,并定义该椭圆的形状。)开普勒还发现了行星轨道大小与行星绕太阳公转周期之间的数学关系。 1687年,牛顿为开普勒定律给出了更深入、更清晰的物理根据。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以物体间的相互吸引为基础,证明环绕某一物体运动的天体,它的运动轨迹呈椭圆形,且椭圆轨道大小取决于该物体的质量。学过天文学基础的对这条定律都不会陌生,而这条定律也是盖兹计算出超大黑洞质量的依据。她多年的精心观测数据,准确地描绘了环绕银河系中心运动的恒星椭圆轨道;然后盖兹利用牛顿的理论计算出位于银河系中心位置的物体质量(牛顿定律的理论基础如今已被广义相对论所取代。广义相对论虽然预言了黑洞,但牛顿的理论用于计算绕超大质量黑洞运动的恒星轨道已足够准确。)了解这些轨道,对于测量超大质量黑洞附近强大引力中的精细结构常数,至关重要。该常数与引力的关系,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以便修改标准模型或广义相对论,从而解决当代物理学中的两大难题:暗物质和暗能量。 这种特殊的研究正契合我们对自然基本常数的更大范围的长期研究。这其中的每一个自然基本常数都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最深层理论的范围或尺度的信息。和其他常数一起,精细结构常数(以希腊字母α表示)出现在隶属基本粒子量子场论范畴的标准模型中。α的数值,定义了光子和带电粒子之间电磁力相互作用的强度;而电磁力则为宇宙基本力之一,其他宇宙基本力还包括引力、强核力和弱核力。电磁力决定了质子之间的排斥程度以及电子在原子中的行为。如果α的值与我们所知的值相差很大,那么这会影响恒星内部的聚变是否会产生碳元素、或者原子是否可以形成稳定的复杂分子。这两者都对生命至关重要,也侧面说明了α的重要性。 其他常数则代表了其他主要的物理理论:真空中的光速(表示为“c”),对相对论至关重要;马克斯·普朗克推导出的常数(“h-bar”或ħ = h/2π)描述了极小的量子效应;以及牛顿理论和广义相对论中的引力常数“G”,决定了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1899年,普朗克仅以这三个常数,定义了一个仅基于自然属性、不涉及任何人造属性的通用测量系统。普朗克写道,该系统对于“任何时代、所有文明——无论是外星文明还是非人类文明”,都将是相同的。 普朗克根据c、ħ和G推导出长度、时间和质量的自然单位:Lp = 1.6 x(10的-35次方)米、Tp = 5.4 x(10的-44次方)秒,以及Mp= 2.2 x(10的-8次方)千克。虽然这些单位因量级太小而在实际中鲜有应用,但它们却有概念上的意义。在当今的宇宙中,基本粒子间的引力相互作用太微弱而无法影响它们的量子行为。但是,只需将物体分开一点点的普朗克长度Lp(小于基本粒子的直径),它们之间的引力相互作用就会变得足够强,足以匹敌量子效应。这定义了大爆炸之后10的-44次方秒的“普朗克时期”。这段时期,引力效应和量子效应强度相当,因此我们需要一个综合的量子引力理论,而我们当前使用的独立的量子理论和引力理论则不适用。 但是,对一些物理学家来说,c、ħ和G并非真正的基础,因为它们仍取决于测量的单位。比如,在公制单位中,c为299792千米/秒;而在英制单位中,c为186282英里/秒。这说明,物理单位有文化的差异,而非自然界固有的。(1999年,NASA的火星气候探测者号坠毁,原因就是两组科学家团队忘记检查另一个团队使用的是哪一个测量系统。)但是,纯数字的常数可以在不同文化之间完美转换,甚至跟外星人的测量单位也可以完美转换。 精细结构常数α因其所具备的纯数字性而受到关注。1916年,在计算氢原子中单个电子在量子能级跃迁时释放或吸收的光波长时,研究人员引入精细结构常数。尼尔斯·玻尔的早期量子理论预测到了主要波长,但光谱还显示了其他特征。为了解释这些特征,德国理论物理学家阿诺尔德·索末菲在氢原子的量子理论中加入相对论。 他的计算依赖一个被他称为精细结构常数的数字。该数字包括ħ、c,以及基本电荷e(另一个自然常数);还有真空电容率ε0。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组合中,物理单位竟全部抵消,仅留下纯数值0.0072973525693。 艾萨克·牛顿
索末菲只是将α用作一个参数。但是精细结构常数真正受到关注,要等到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当时,法国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在相对论量子力学的高级研究中再次引入精细结构常数。接着,该常数又出现在英国天文学家亚瑟·爱丁顿的万有理论中。他希望将量子理论与相对论相结合,以推导出宇宙的属性,如宇宙中的基本粒子和各种常数,其中就包括α。 爱丁顿所用方法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于,他考虑的是1/α,而非α本身。因为他的分析表明,1/α必然是一个整数,且是一个纯数字。这与现代测量结果一致,1/α的值等于137.1,非常接近137。而爱丁顿计算得出的结果是136,数值之接近足以引起人们的兴趣。但是,进一步的测量证实1/α的值等于137.036。爱丁顿试图解释这其中的差别,但结果并不能令人信服。又因为或这或那的原因,爱丁顿的理论终究未能存续下来。 但是α和数字“137”之间的联系保留了下来。也因此,理查德·费曼将“137”称为“神奇数字”。当然他说的神奇数字,跟数字命理学毫无瓜葛。事实上,α的神奇之处在于,我们虽然知道如何测量α的值,但却不知道如何从已知的任何理论中推导出α的值。尽管如此,α的值在量子电动力学(电磁量子理论)中至关重要。 所以,大家一致认可,α是一个重要的自然常数。现在,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些常数的值,那么物理学家们又要问了,这些常数的值,真的永远不变吗?1937年,狄拉克在思考宇宙基本力的时候,猜测α和G的值将随着宇宙年龄的增长而改变。另一个更古老的猜测是,这些常数是否在整个宇宙中有变化。 变化的“常数”,不仅会改变基于这些常数的标准模型和宇宙论,也会改变广义相对论。这些理论等等都无法解释暗物质和暗能量。在“我们的宇宙是经过了’微调’,从而孕育生命”这样的观念中加入α的角色,以及相关的想法——如在众多宇宙中,我们存在的那个宇宙具有最完美的α值等等,这一切都激发了人们对自然常数的研究,其中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精细结构常数α。 地球上的测量几乎可以肯定α的值是固定不变的。一个更具挑战性的项目是在天文距离上测量α的值。这也决定了宇宙早期时候的α值:因为数十亿光年外的光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从年轻的宇宙到达现在的我们这里。自从1999年以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约翰·韦伯和他的同事就一直在收集来自被称为“类星体”的遥远星系核心的光,以测量α的值。类星体中心的黑洞会吸收发光的尘埃。这些来自类星体的光穿过星际云,然后原子特征波长在气体云中被吸收。分析该波长可以得出遥远位置的α值,道理和我们在地球上用氢波长首先确定α一样。 韦伯的早期研究结果显示,在过去60亿年或更长时间里,α增加了0.0006%,并且这个增加的值取决于测量位置相对于地球的距离。2020年发布的研究结果显示,现在的α和130亿年前(那时宇宙的年龄不过8亿岁)的α相比,有微小的变化。种种研究结果还表明,α也随空间方向的不同而改变。但总体而言,实验误差太大,任何测量到的α值的变化,其准确性有待商榷。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变化非常微小。 现在,我们可以测量强引力场中的α值。理论上来看,强引力场中的α值应该会改变。已知最强的引力场来自黑洞;宇宙飞船只有在达到无法企及的光速时才有可能逃离黑洞。白矮星的周围也伴有强大的引力场。2013年,新南威尔士大学的J.C。布伦格特和韦伯等人一起分析了来自一颗白矮星的光谱数据,得到的α值相比地球的α值,存在0.004%的变化。 但是,一直到今年,希斯和盖兹等人发布共同研究之前,从未有人测量过超大质量黑洞附近的α值。盖兹在凯克天文台的观测数据协助研究人员选择了五颗特殊的恒星。它们的轨道会使其接近超大质量黑洞,从而最大化该超大质量黑洞的引力作用。另外,由于周围的恒星大气,这几颗恒星的光谱显示出强吸收特性。这有助于研究人员针对每一颗恒星,从吸收波长中,推导出α的值。最终的复合结果再次表明,超大质量黑洞附近的α值,与地球上的α值相比,存在仅0.001%甚至更小的变化。 虽然测得的α值变化很微小,但针对超大质量黑洞周围引力场中不同位置的五颗恒星的研究,带来了新的结果;该研究也对理论预测做了早期测试,即α的变化,与引力势的变化,成正比。(引力势即引力场中存储的能量。) 就目前而言,在时间、空间和引力下,测得的α值的变化仍太小或存在不确定性,因而无法指导物理学家转向新的理论,甚至都不足以激发新的猜测,比如宇宙深处或黑洞附近是否有生命存在。 不过,知道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宇宙中,这个特别的自然常数可以保持稳定,兴许也是一种安慰。但是,如果在银河系的超大质量黑洞周围观测到α值的更大变化,这或许将标志着新物理学的起点。希斯在他的邮件采访中写道,如今,他的目标是更深入地研究黑洞的引力场。他计划在2021年进行一项新的优化测量,以“观察与黑洞距离更近的恒星,因为距离更近,这些恒星也将经历更强的引力势……但是利用当前的技术,对于十分靠近黑洞的恒星,我们很难获得较好的光谱观察数据”。但希斯仍旧相信,他可以将测量误差减少10倍。 盖兹那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仰仗于观测技术和光谱技术的巨大进步。可以肯定的是,以这个成功项目为基础的技术改进,将继续加深我们对超大质量黑洞的研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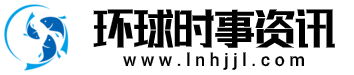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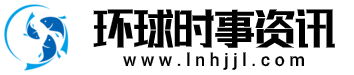
 主页 > 新闻 > 科普 >
主页 > 新闻 > 科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