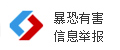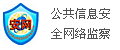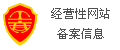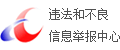|
今年,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所属的北京市学习科学学会要举办读书活动,我父亲傅惟慈翻译的书籍荣幸地被选为读物。 他的专业是外语,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北京大学留学生高等预备班教书,培养准备出国的学生,后来这个机构又升级为语言学院,直至今天的北京语言大学。 教学之余,他勤奋地干着他热爱的翻译工作。我记得,他翻译过一本匈牙利剧本《小花牛》,那时我可能只有五六岁。当时收音机居然播放这部广播剧,广播员字正腔圆地说“翻译傅惟慈”,我听到后,着实兴奋了好一阵。 直到现在,我的脑子里时不时浮现这样的画面:在黑夜中,一盏昏暗的老式桌灯的灯光,映照着父亲伏案工作的背影。那种绿色玻璃灯罩的台灯,现在只能在电影、电视剧中看到。他一生翻译了二三十本外国文学作品,其中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翻译家李文俊的夫人张佩芬告诉我,他们夫妇二人当时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出版《世界文学》杂志。“我们看到你父亲翻译的《布登勃洛克一家》这本书,内容真是太好了,我们马上决定把选段登在我们的期刊上,后来才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我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热爱中国的文化人。1969年底,北京语言学院搬到天津附近的茶淀农场,父亲、母亲和妹妹也到了天津。我当时在山西,多次探望过父亲。父亲抓紧时间给我补了些古典文学缺口,见面时就给我讲解《聊斋》等。他作为一个外语匠人,枕边永远放着中国古典文学书籍、诗词、章回小说,等等。他爱中国文化、爱中国山川大地、爱同胞重亲情,这是他骨子里的东西。在此期间,我父亲到了一个木器厂学做木工,有了些木工基础,后来回到北京后还为自家做了桌子、沙发等物件,受到大家的称赞。 改革开放后,他翻译过的书也都陆续再版。他重新站上讲台的同时,又翻译了很多本相当畅销的外国文学作品,这是他人生的春天。 再讲几个小小的翻译趣闻。现在听起来都不是事,但当时搞翻译的人,因为没有机会出国,没有在一个真实的外语环境中学习过,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问题。《布莱顿硬糖》是格雷厄姆·格林的著名小说,曾被搬上银幕,但英文原文是“Brighton Rock”。大家都知道“rock”明明是“岩石”的意思,这又是怎么回事?父亲就去找了外国留学生询问这个问题,后来知道,原来Brighton这个地方一直生产一种糖块,因为是硬的,所以习惯把这种糖块称为“rock”。在他翻译另外一本书时出现了“去药店买了个三明治吃”,如果直译会让人莫名其妙,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英国的药店也卖人们常用的日化产品、牙膏、洗头水等,还有一个柜台卖吃的,去药店买三明治就顺理成章了。 改革开放的春天,不但沐浴了中国,也浇灌了他的人生。父亲终于有机会迈出国门,他去德国洪堡大学教了几年书,去英国讲学,BBC还为他开了一个专栏。他翻译一些故事,每天去播讲,其中的重头戏就是马克思的故事。在英国,他还见了著名作家格雷厄姆·格林。我父亲翻译了他的作品《问题的核心》。 他去世前几年,漓江出版社的老编辑刘硕良有一个出版计划,找了当时仍健在的10个翻译家,挑出自己最满意的作品,给每个人出一本《自译集》。他挑出他最喜欢的作品、片段打印出来,我读他听,然后对个别地方作修改,这是我唯一一次有机会细细地读了他的一些作品,真有让我拍案叫绝的地方,最终出了一本非常珍贵的《自译集》。 他是一个极其热爱生活的人,爱好广泛,干什么都要干出名堂。篇幅有限,我挑着说几件事。父亲特别喜欢古典音乐,在没有接触到别的音乐形式前,他小时候喜欢过大鼓书、梆子戏,等等。自从听到西方古典音乐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后来,他的大部分稿费都去王府井的外文书店买了进口的密纹唱片。著名乐队、演奏家、指挥家的唱片,他一定要买。所有的唱片都制作精美,封面都是绝好的艺术品,更不要说音乐本身。每个周日的早晨,我都在大声响着的音乐中醒来,其实这也是一种文化的熏陶。我五六岁就开始学习小提琴,虽然不用功,拉得也不怎么样,但对音乐的喜爱,让我一直觉得是件很幸福的事。 后来,年过70岁的他跑过印度、游过伊朗,完全是自助游。祖国的名山大川更是大都留有他的足迹,他的摄影作品被很多专业杂志刊登。晚年的他跑不动了,又倚仗外语“功力”积攒外国钱币和纪念币,里面的故事深深吸引着他。慢慢地,他在全国的集币界也成了数得上的人物。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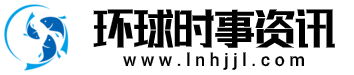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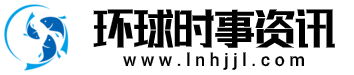
 主页 > 新闻 > 科普 >
主页 > 新闻 > 科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