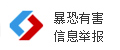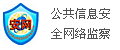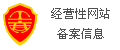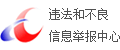|
为什么说特朗普政府等提出的任由病毒发展的建议会带来“不计其数的死亡和痛苦”。 2020年5月,新冠肺炎(COVID-19)大暴发重创了巴西城市玛瑙斯。医院不堪负荷,居民开始在附近森林为逝者挖新的墓地。但到了8月,形势有所扭转。虽然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在6月初开始放松,但这座人口200万的城市已经将超额死亡数从每天约120降至近乎为零。 9月,两组研究人员发布了预印本论文,称玛瑙斯夏季末的病例增速减慢,至少一部分原因是社区里的大量人口已经有过新冠病毒(SARS-CoV-2)暴露并免疫了。巴西圣保罗大学免疫学家Ester Sabino和她的同事对玛瑙斯血库里的6000多份血样进行了检测,从中寻找新冠病毒抗体。 “我们发现,被感染的人口比例很高——第一波疫情快结束时达66%。”Sabino说。她团队的结论是[1]:如此高的感染率意味着当前对病毒仍然易感的人群已经很小,以至于无法触发新一轮疫情——这种现象也被称为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巴西的另一个研究团队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2]。 美国新泽西州的一场特朗普竞选集会。特朗普曾表示支持群体免疫的抗疫策略。来源:Spencer Platt/Getty
来自玛瑙斯的这些报道,以及对疫情初期遭受重创的意大利部分地区的类似推断,助长了寻求群体免疫的呼声。这类计划建议让大部分社会回归常态,同时采取一些措施保护重症风险最大的人群。本质上就是任由新冠病毒自然发展,支持者说。 但是,流行病学家再三斥责这种想法。“向病毒投降”并不算防御计划,加州斯克利普斯研究所的免疫学家Kristian Andersen说。这种做法会夺去很多无辜的生命,也不保证社会就能更快地恢复常态,“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成功地实现过群体免疫,而且这会给人类带来无法承受且没有必要的大量死亡和痛苦。” 虽然饱受批评,这种想法还是不断地从许多国家的政客和决策者的脑海中冒出来,包括瑞典、英国和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月提到群体免疫时态度积极,还误将其称为“从众心理”(herd mentality)。甚至还有一小部分科学家也在推波助澜。10月初,一个自由主义智库和一个少数科学家组成的团队联合发布了一份名为《大巴灵顿宣言》(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的文件,呼吁让新冠肺炎重症风险较低的人回归正常生活,让新冠病毒传播到一定程度后,便可实现群体免疫。文件还称可以用一些措施来保护高危人群,如老年人,但基本未作详细说明。宣言的起草者得到了白宫的支持,但《柳叶刀》的另一组科学家也发布了反击备忘录,称群体免疫是“没有科学证据支持的危险谬论”[3]。 扬言要让新冠病毒不受干预、自然发展的人,基本上都对何谓群体免疫、实现群体免疫的最佳方式存在误解。在此,《自然》就这个备受争议的概念澄清五个问题。 何谓群体免疫? 当病毒遇到的都是受到保护、不会被感染的人群时,病毒就无法扩散,也就实现了群体免疫。一旦有足够比例的人口不再易感,新的疫情就会逐渐消失。“你不需要让所有人都免疫——只要让足够人口免疫就够了。”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的流行病学家Caroline Buckee说。 一般来说,群体免疫是作为大范围疫苗接种计划的理想结果来讨论的。当接种诱导的免疫力在人群中达到较高水平时,那些不能接种或对疫苗反应不够的人群,比如免疫系统低下的群体,也能受益。Buckee说,许多医疗专家讨厌“群体免疫”这个词,而更倾向于叫它“群体保护”(herd protection)。因为群体免疫不会真的让所有人都对病毒有免疫力,它只是降低了易感人群与病原体接触的风险而已。 公共卫生专家一般不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把群体免疫当作一种可用的工具。“这个词现在被用来表示要让多少人感染,才能给这一切划上句号,这令我有点困惑。”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流行病学家Marcel Salathé说。 如何实现群体免疫? 流行病学家可以估算出需要多大比例的人口免疫,才能实现群体免疫。这一阈值取决于基本再生数R0,即在完全易感、充分混合的人群中,一名感染者平均能感染的人数,香港中文大学传染病流行病学家、数学建模师郭健安(Kin On Kwok)说。计算群体免疫阈值的公式是1–1/R0,即每位感染者能感染的人数越多,就要有更高比例的人口免疫,才能实现群体免疫。打个比方,麻疹的传染性很强,R0一般在12到18之间,计算得出的群体免疫阈值为总人口的92%到94%。病毒的传染性越低(再生数越低),这个阈值也越低。R0假设所有人都对该病毒易感,但这其实会随疫情发展而发生变化,因为有些人在康复后会获得免疫力。出于这个原因,这类计算中有时会用到R0的另一个版本——有效再生数(缩写为Rt或Re),它将群体的易感性变化考虑了进来。 虽然代入数字,公式就能给出实现群体免疫的一个理论数字,但在现实中,群体免疫并不是到了那个点就能自动完成的。恰恰相反,群体免疫更应被视作一个梯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流行病学家Gypsyamber D’Souza说。而且,由于R0和对病毒易感的人数等变量可变,所以群体免疫并非一个稳态。 即使在人群中实现了群体免疫,大规模暴发依然会发生,比如在疫苗接种率较低的地区。“我们在流传着疫苗安全性谣言的一些国家见过这种情况。”Salathé说。“你发现部分地区的接种率开始下降,然后本土疫情暴发,有些规模很大,即使你已经在严格的数学意义上实现了群体免疫。”终极目标应该是预防人们生病,而不是去达到模型中的那个数字。 新冠病毒的群体免疫阈值有多高? 能否实现群体免疫,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口的整体情况。阈值的计算对R值非常敏感,郭健安说。6月,他和同事在《感染期刊》(Journal of Infection)上发表的给编辑的信中阐释了这一点[4]。郭健安及其团队利用3月份的新冠肺炎每日新增病例数,估算了超过30个国家的Rt,随后在这些Rt的基础上计算了每个国家人口要达到的群体免疫阈值。其中,Rt为6.64的巴林阈值最高——85%,Rt为1.06的科威特最低,只有5.66%。科威特的阈值很低,反映出它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在当地实行宵禁,禁止多个国家的商业航班等。郭健安说,如果科威特取消这些措施,群体免疫阈值就会上升。 巴西玛瑙斯的一处墓地,拍摄于6月。整个城市在4月和5月受到了疫情的重击,目前的病例数正再度回升。来源:Michael Dantas/AFP via Getty
关于群体免疫的计算,比如郭健安的计算结果,它们所基于的假设可能无法反映现实生活,美国西北大学研究传染病的网络科学家Samuel Scarpino说。“大部分群体免疫的计算根本不考虑人类行为。它们假设没有干预、没有行为改变,诸如此类。”他说。这意味着,如果人类行为出现的短暂变化(比如保持物理距离)让Rt下降,那么“一旦行为恢复正常,群体免疫的阈值也会改变”。 目前对新冠病毒阈值的估计在10%到70%之间——或是更高[5,6]。不过,从算出阈值下限的模型来看,其假设的人类社交方式可能是无效的,Scarpino说。阈值的下限假设接触者较多的人会先感染上,也正是因为他们接触的人多,他们会把病毒传给更多人。而当这些“超级传播者”对病毒获得免疫力后,易感人群中的传播链就会大大减少。“于是,你很快就达到了群体免疫的阈值。”Scarpino说。但如果你发现所有人都能成为超级传播者,那么,“能把估算值降到20%或30%的假设根本就不准确,” Scarpino解释道。结果是,群体免疫阈值将逼近60%-70%,这也是大部分模型计算的结果(比如参考文献[6])。 发生在监狱和邮轮上的超级传播者事件似乎清晰地表明,新冠肺炎一开始是大范围传播,然后再在聚在一起、未接种的人群中慢下来,Andersen说。在加州的圣昆廷州立监狱(San Quentin State Prison),超过60%的人在疫情被遏制住前基本都感染上了,所以并不是什么30%的人感染后,疫情就会神奇地消失,Andersen说。“没有什么神秘的暗物质在保护人类。”他说。 虽然科学家可以估算群体免疫的阈值,但他们无法知道实时数字,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流行病学家Caitlin Rivers说。事实是,只有对数据进行回顾性分析,才能对群体免疫得出确定的观察结果,而这最久可能要等到十年以后,她说。 群体免疫真的有用吗? 许多研究人员认为寻求群体免疫是个糟糕的想法。“尝试通过针对性的感染实现群体免疫简直荒唐透顶,”Andersen说,“在美国,这可能要死一两百万人。” 就在5月的第一周,玛瑙斯的死亡率一度攀升至前一年的4.5倍[7]。到了8月,病例数增速减慢让人为之激动,但如今的数字似乎又开始回升。这种回升说明,说玛瑙斯人口已经实现群体免疫的推测“其实根本不对”,Andersen说。 死亡只是这其中的一部分。得病的人面对的是严重的健康和经济后果,而且很多康复者都报告了持续的健康影响。玛瑙斯有超过5.8万名新冠病毒感染者,而这背后又有多少疾苦。 在疫情初期,媒体曾报道瑞典打算让民众维持正常生活,尝试群体免疫的策略,但瑞典卫生与社会事务部长Lena Hallengren表示,那是个“误解”。群体免疫是“病毒传播发展的一种潜在结果,无论是在瑞典还是其他国家”,她在给《自然》的一份书面声明中如此写道,但它“不是我们策略的一部分”。她说,瑞典的策略是采取与大部分国家相似的做法:“鼓励保持社交距离、保护弱势群体、开展检测和接触者追踪、强化卫生系统以应对疫情。”尽管如此,但瑞典很难称得上一个成功典范——来自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显示,瑞典每10万人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是邻国挪威的10倍多(瑞典58.12/10万人,挪威5.23/10万人)。而瑞典的病死率,即与确诊病例数的比值,也至少是挪威和丹麦的三倍。 群体免疫还面临哪些阻碍? 通过让病原体在社区内传播来完成群体免疫,这个概念基于康复者会自动免疫这一未经证实的假设。就新冠病毒而言,感染后似乎会获得某些功能性免疫力,但“要理解免疫应答的持续时间和作用,必须对人群进行纵向随访,而现在才刚刚开始”。Buckee说。 此外,目前尚无绝对可靠的方法来测量对病毒的免疫力,Rivers说。研究人员可以检测人体是否产生了新冠病毒特异性抗体,但他们无法获知这些免疫力能保持多久。引发普通感冒的季节性冠状病毒所诱导的免疫力会递减,而且貌似只能保持一年,Buckee说,“可以合理地假设,这次的病毒也差不多如此。” 近几个月出现了有人在初次感染后二次感染的报告,而这种再感染发生的频率以及它们的致病能力是否会减弱都还有待回答,Andersen说。“如果感染者在一年后再度易感,你将永远无法靠自然传播达到群体免疫。”Rivers说。 “这里没有魔法棒可用,”Andersen说,“我们必须直面现实:我们从来没有通过让新病毒自然传播实现过群体免疫,可惜的是,新冠病毒也不例外。”疫苗接种是实现群体免疫的唯一符合伦理的方式,他说。多少人需要接种——接种频率是多少——将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疫苗有效性如何、保护力能维持多久。 人们一开始对强制措施感到厌倦和不满,比如增加社交距离和封锁管控——这可以理解,但在疫苗问世之前,这些都是最有力的抗疫工具。“不是所有人非得感染这个病不可,”D’Souza说,“有很多原因值得我们坚定信念。如果我们能继续实施风险管控举措,直到有效疫苗出现,我们就一定能挽救生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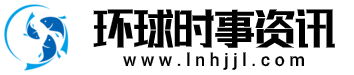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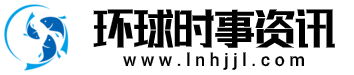
 主页 > 新闻 > 科普 >
主页 > 新闻 > 科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