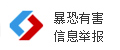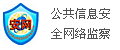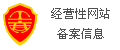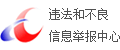|


江南的春,总爱和“茶”紧密联系。当春风使出浑身的解数,将长江以南的寒冷往北驱赶时。山坡上、岭坝上的茶树,都探头出门相送。作为常绿草木中的名门望族,茶树总显得彬彬有礼,温情有余。就在那“春风吹又生”中,片片嫩芽携着早春的信息,传遍了整个大地。 和所有的植物都不一样,那是老叶出嫩芽,一叶顶着一叶,一年最是新春好。那带着最初信息的芽叶,“犹抱琵琶半遮面”。它们听得懂鸟语嗅得到花香,它们衔着春光携着云雾,终在一场春雨后,生出雀舌般的叶芽。一副水嫩水嫩的面孔,如出水芙蓉般隽秀,看着就让人亮眼可心。那一片片长形或椭圆形的茶叶,如春天的请柬,盛邀着人们赶来采茶。 有茶树的地方就有青山绿水。那些茶树总爱长在向阳的山坡上,如犍牛饮水,将头扎进清凌凌的山溪,尾巴却在身子后面甩打出一阵山风。那里阳光明媚,风清云淡,草木葱郁,景色迷人。 我曾在苏州碰见过早春的茶园。一面坡上,层层叠叠。一株株茶树,密密麻麻,绿的耀眼。戴着斗笠的茶农,斜挎竹兜,站在茶园里如一棵松挺立。身子似乎纹丝不动,手却如鸡吃食般快捷,灵巧得如水里的游鱼,从那些茶树上一一走过,一枚一枚的嫩芽便被请进挂在腰间的竹兜。人们常说:“一斤碧螺春,四万春树芽。”我很难想象,这一斤茶叶,需要在穿梭、弯身、采摘、放入中轮回四五万次才行,那是怎样的一个琐碎和不厌其烦。他们额头热气腾腾,如云雾散开,笑容里溢满茶香。采过茶叶的树便没了春的盎然,只有春的继续。远远望去,绿色的茶园里,那些埋头的采茶者如一朵朵各色的花,绣在绿色的锦缎上,分外好看。 采茶不易,制茶也不简单。我曾在云南参观过传统的手工制茶,那岂是一个辛苦所能表述?采摘下来的茶叶特别娇气,需要尽快去除水分,否则就会发苦生臭。温暖的阳光下,一片新绿挤满了大大小小的茶簸,经过日光萎凋或高温炒制后,就在茶簸里,被茶农用双手轻揉着。那是一种看似有力却是柔软的揉法,手粗糙中见细致。不同的茶,其揉捻程度也不一样。大多数的茶叶被滚动揉成了卷曲状,也有以布巾包裹茶叶使其成为一圆球状,再以手工或布球揉捻机来回搓压、团揉,最终形成半球形或球的。有些茶叶还进行摇青,将萎凋的茶叶放在竹筛内,先轻后重,来回筛动,让叶片在摩擦碰撞中,气味相投,渐渐氧化。不同的茶摇青的手法不一样,次数也不一样。这一连串的晾青、杀青、揉捻、渥堆、干燥、紧压等过程,让茶叶如孩童一般,逐渐成长。但它还没有真正成为茶叶,必须再经过筛分、剪切、拔梗、整形、风选、覆火、熏花、焙火、掺和、陈放等一系列过程,才算完全制成。 当一片片茶叶泡入水中,氤氲的不仅是满鼻清香,还有天地灵气,日月精华。茶中有山,茶里藏河,可谓是胸有丘壑。一壶茶在手,如天人合一,如抚日托月,如捧着千山万水。郑板桥品茶曾邀“一片青山入座”,苏东坡喝茶感叹“从来佳茗似佳人”。它是一味解毒的药,让“神农尝百草”;它走过了饮汁食叶的羹饮,最终变成今天享誉世界的三大饮品之一;它是茶马古道的千年穿行,让生命历经枯萎、重生、绽放,如人世的修炼;它缔结出了中华血性与千年文化,让世界幻想着东方的神奇。 一片茶叶,看起来细小、纤弱,无足轻重,却又是那样地微妙、坦荡、豪放。它感受了土地和手掌的温度,行走万里,与水融合,呈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它沟通了天地生命,融合了人与自然,传递出一缕醉人的心香。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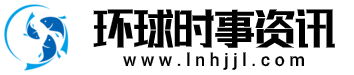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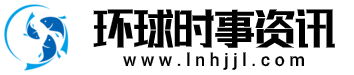
 主页 > 新闻 > 科普 >
主页 > 新闻 > 科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