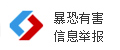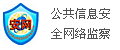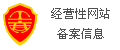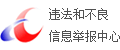|

发育成熟后的下一代榕小蜂正要从榕果内钻出。王刚摄 专一,原本是人类的一种高尚品德,但人们也想在自然界寻找这样的“美丽心灵”。科学家曾在动植物协同演化历史上发现过一个极佳案例——榕树与榕小蜂。
榕树是陆地上种类最丰富、生态型最多样的木本植物群,全世界已知的有800多种。有趣的是,一种榕树只让一种榕小蜂传粉,而一种榕小蜂一生也仅给一种榕树传粉,它们之间有着极为严格的专性关系。
不过,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以下简称版纳植物园)的科研团队在十几年里,陆续搜集到了榕小蜂越来越多的“黑历史”。他们联合了国内外12家研究机构,利用基因组测序分析,证实了榕小蜂在这段关系中,会时不时地“开小差”,而且已经持续了7500万年!
最近,《自然—通讯》就报道了这个符合人类浪漫想象的科学故事是如何被打破的。
难以动摇的专性互惠关系
榕树,又叫无花果树。由于花都藏在内部,人们通常看不到榕树开花就发现它结了果。榕果顶端留有通道,可在花期释放特殊气味,吸引并允许特化的传粉榕小蜂钻入。榕小蜂在榕果内为雌花授粉的同时,还会在一部分雌花子房内产卵,生儿育女,未被榕小蜂产卵的雌花则发育成种子。
榕树—榕小蜂一直被视为代表了已知的最极端和最古老(约7500万年前)的专性互惠关系,它们也成为了研究生物间互惠共生和协同演化的最佳模式材料。
这种关系为什么会形成?科学家提出,不同种传粉榕小蜂对雌花期榕果的特异挥发物的识别是实现传粉者隔离的主要机制。
他们还认为,紧密的传粉者特异性加速了宿主植物的多样性,因为传粉者对植物进行了分化选择,增强了生殖隔离。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世界上会有如此多种类的榕树。
然而,支撑这一论断的证据并不十分严密。
“缺点是,过去的采样太稀疏。”版纳植物园研究员王刚解释,“除了基于有限的榕树物种上有限的榕果调查,特别是在系统与进化生物学研究领域,大部分现有的系统发育推断都是基于相对较少的、信息有限的基因数据,这些基因对关键基础节点的支持能力很弱。此外,这些研究缺乏遗传深度和全面的取样设计。”
在榕树—榕小蜂的专性传粉关系中,科学家也逐渐发现了特例。
2008年,版纳植物园的科研人员观察到,有两个不同属的非传粉小蜂钻进了环纹榕组(Conocycea)的隐头果内,并有效地为它传粉,其中一个种传粉效率甚至超过传粉小蜂。此后,又有科研团队经过实验发现,榕果特异挥发物并不能保证对传粉榕小蜂的专性吸引。
尽管这些成果陆续发表在学术期刊上,但仍无法动摇当时学界的主流论断。
王刚告诉《中国科学报》:“大多数生物学家认为,这些只是在物种分化阶段出现的错配,或者说,是生态学尺度上的‘噪声’,并不会对演化格局产生影响。”
一榕一蜂、齐头并“进”不存在
如何才能证明,这些少数特例也许并不是演化历史上一个偶然的断面呢?
版纳植物园动植物关系研究组领衔国内外12家研究机构,收集了榕属主干类群15个代表物种的核、叶绿体和线粒体基因组的全序列,运用多种分析方法重建了这些分支之间的系统发育关系,并鉴定了在整个榕属植物的演化历史中核基因组中可能记录的杂交案例。结果出人意料。
论文通讯作者之一的王刚表示,团队第一次发现,榕树主干类群之间从7500万年前开始就不断发生着杂交渐渗,不论古老还是年轻的类群。
在一个专性传粉的共生系统中,科学家很难想象可能存在如此大规模的杂交事件。而这也暗含着,榕树—榕小蜂的一对一关系,并没有过去认为的那么牢靠。
接下来,科研人员用已发表的接受度最高的两棵对应传粉榕小蜂的系统树,和这项研究中得到的任意一种榕树系统树进行了逐一对比,结果发现所有榕蜂系统树都存在明显的不一致性。
很遗憾,一榕一蜂、齐头并“进”的故事从来就不存在。
“对某一种榕树来说,主要对应的还是一种榕小蜂。但是,几乎所有传粉榕小蜂都存在转移宿主的可能。而且,榕小蜂‘开小差’的对象很宽泛,不论同域或者不同域、近缘或者远缘,都有可能。”王刚表示,个体层面的小概率错配事件推广到物种层面,就成为了一个普遍发生的现象。
研究人员的榕蜂共进化分析还推测出,传粉榕小蜂的宿主转移事件发生的频次远高于榕蜂协同成种事件的频次。这都和检测到的榕属主要类群间频繁杂交渐渗的格局形成了很好的对应。
可见,榕—蜂物种的关系网络比过去认为的要复杂得多,在王刚看来,这不失为一种出色的演化策略。“一旦环境巨变,发生物种灭绝,不在一棵榕树上吊死的榕小蜂,才不至于‘团灭’。”
这项研究打破了学术界对榕树—榕小蜂这一经典专性传粉系统的长期共识,它提示,可能是传粉者的宿主转移而不是协同成种主导了榕树—榕小蜂协同演化的历史。而这种模式对其它专性或泛性传粉系统的多样化研究也有借鉴意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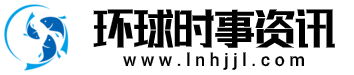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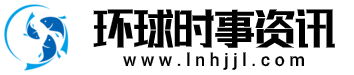
 主页 > 新闻 > 科普 >
主页 > 新闻 > 科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