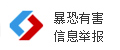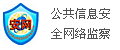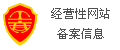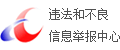|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张掖的女孩子曾对我说,她会在张掖城头等我。
她说曾看见自己在张掖城头迎接我,并和我在古城楼前相拥。
我不知道是她真有预见未来的能力,还是她梦中所见,又或者仅仅是她内心所盼望的景象幻化,但这已经对我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我感觉自己就像薛定谔实验里的那个放射性物质开关,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放出毒气,打开那个盒子以后,一半的几率猫会被毒死,一半的几率能存活。
现在的她对我是量子态的,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可能存在过,也可能只是梦,一切皆有可能,但假如我去了张掖,这存在与否便会落到实处,便如打开了薛定谔的盒子,是死是活,一望而知。
如果真如她所说,她在高高的城头迎我,那我当然热泪盈眶长歌当哭,但假如她不在,那我心中长久以来的那份执念,便没了安放的所在。
遇见她之前我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彻底的无神论者,不相信世间有超越科学的事件存在。那时候我很年轻,无知又无畏,不信子不语,任何妖魔鬼怪神仙奇谈都能被我归类于封建糟粕或者机缘巧合。
但世上的事就是有那么多机缘巧合,就像本来我和她根本不会有重合的轨迹,也不可能会相遇,她是甘肃张掖人,我是江浙人,一南一北背道而驰,她从未离开过中国西部,而我从出生起就一直在中国东南。
那一年她正好考到川大中文系中国古代文献专业读研,而我刚从国企跳槽到那家著名的韩国企业,被派到成都驻点。我喜爱打篮球,老是跑到川大去打球,那时候川大中文系的水平是国内顶尖的,经常有大作家大学者去讲课,我也爱凑热闹,偶尔会跑去听听。
我记不得那次是听谁的课了,不知是口才不好还是名不副实,听得我昏昏欲睡,坐的位置又在中间,我脸皮薄不好意思在众目睽睽之下溜出去,那时候没有智能手机可玩,只能不停地转着笔,一不留神,把笔转到了前面那排的地上。
她弯腰把笔捡了起来,回头递给我,那一刹那,我愣住了,都忘记了去接笔,她捂着嘴笑了,把我闹了个大红脸。我想她肯定在嘲笑我没见过美女,土老帽一个,我感觉我的表现屌丝极了,想解释,又不知道从何说起,幸亏她瞄了我一眼之后就转回了头。
她当然算美人,是那种清丽的长相,瘦而白,但我从小江南水乡长大,又怎会没见过美女呢,我之所以如此失态,是因为她的脸,太熟悉了!尤其她嘴角那颗芝麻般的痣,在我梦里不知出现过多少回。
有段时间我一直做一个梦,梦里有个女孩子转过头对我粲然一笑,那笑容如此惊艳,如日出东方光芒四射。
我隐隐约约记得我曾见过她,那时我好像十六七岁,在上初中,和一个哥们去逛百货公司,八十年代的小城只有一家百货公司,一到节假日,人挤得满满当当,大家都是摩肩接踵一步一挪。我兜里没钱,纯粹是赶热闹,后面人推挤着我,我便推挤着前面,走在我前面那个女孩子突然转过头来对我一笑。那一刻好像有个新世界的门为我打开了,她笑得那么好看,笑得好像我心里有什么东西突然生了根,发了芽,开了花。
等我回过神来,她已被人流裹挟着不见了踪影,我只记得她那张鲜花一般绽放的脸,只记得她嘴角有一颗细如芝麻的黑痣。以前我觉得人脸上长了痣就显得邋遢猥琐,可长在她脸上却那么俏皮风情。
时间久了,我的记忆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搞不清到底是因为遇见了她,所以她才入了我的梦,还是根本就没有遇见她这回事,根本就是梦见她次数多了,把梦当成了现实。
那天公开课上她捡起笔转过头来那一瞬,我惊呆了,我在这个时空又与她重逢,她的脸与我的梦重合在一起,严丝合缝。
下了课,我纠结了半天,想问问她是不是少年时遇见的那个笑容像鲜花一样绽放的女孩,又不知道该怎么说,扭捏来扭捏去,礼堂里人都快走光了,幸好她还在慢慢收拾东西,我鼓起勇气拿笔戳了戳她的肩膀,低声说,我好像见过你。
说完我就后悔了,这个说法实在蹩脚极了,十有八九要被她当成泡她的套路,估计会被她笑死。
结果没想到,她转过身来,认真地看着我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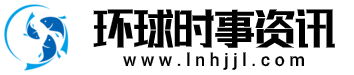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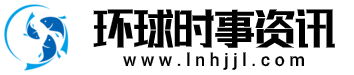
 主页 > 情感 >
主页 > 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