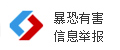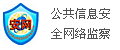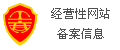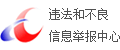|
前年秋末,我在天山南麓西白杨沟骑马。
秋色正好,青黄色的牧草浅浅没过马蹄,白色小花星星点点散落,我在草甸子上来回驰骋,头顶常年不化的天山冰峰,眼前大片大片青翠的云杉林,一气跑了十几个来回,听着风声在耳边呼啸,仍然觉得不过瘾,便拨马向上,穿越高大挺拔的云杉林,纵马上了雪线。
雪线上空气寒冷稀薄,萧瑟荒芜,没有人迹没有信号,与世隔绝,若想逃避纷纷扰扰的红尘,来此虚度时光,想必是绝佳的选择。
一人一马骑到意兴阑珊时,天色已擦黑,刚下到山脚,手机微信叮叮当当响成一片,一条一条翻过,看到其中一条时我突然愣了一下,有人要加我微信,号码陌生,名字却极为熟悉:我是添衣。
皎洁的月儿已高悬雪山之上,整个城市都在雪山脚下静静地匍匐着,好像为这神山皓月所倾倒。开车驶过月下树影斑驳的盘山道时,街灯次第亮起,苍茫的夜空下,远处城市里高楼也一幢接一幢地亮了起来,这些光线蜂涌着朝我扑来,在我心里横冲直撞,仿佛把埋藏在心里最深处的尘埃碎片全震了出来,一幕幕前尘往事,穿透时间迷雾,怔忡着在脑海里重现。
一个走丢了二十年的人,回来了。
1
好多年前,春天曾在我心里头埋下一颗种子,它在岁月里慢慢长成了两片嫩芽,一片停留原地,还有一片,在春风里舒展起身躯,许是觉得春光大好,转回头微笑着说,世界那么大,我好想去看看。于是扇了扇翅膀,便随了春风飞去。
世界真的大,到处繁花似锦,到处人流如织,那片叶子一下就不见了影子,只剩下另一片叶子孤独地写着诗:多么想念你停在我身边的样子,想起来我的爱就不能停止。
那时候读张爱玲的《同学少年都不贱》,只是当一本言情小说在读,觉得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读不出什么特别感受,但年纪越大,回想起来却越有感触。同学少年都不贱,说是年轻时初生牛犊的勇气也好,说是幼稚不知天高地厚的莽撞也好,二十郎当的年纪不在乎贵贱,不在乎门第,即便穷也穷得豪气冲天,哪像现在,就只会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对有些人有些事只敢心里想想,绝不敢踏出一步。
那一段时间我很穷,真的很穷,一穷二白,一日三餐发愁,每个月底看着房东的嘴脸发愁,落寞地躺在房间里看着窗外的月光发愁,幸运的是,那时候有她陪我一起挨穷。
那是整整二十年前,我还很年轻,还有一点点文学的梦想,写一些诗和散文到天南地北的刊物上投稿,有的发表了,有的退回来,归根结底的是退的多发的少。
那时候少年不识愁偏要上层楼,取了个笔名叫秋凉。运气不错,用这个笔名的好几篇散文都发表了,变成了白纸铅字寄了回来,她见了比我还高兴,欣喜地跟我说,从今往后,她就改名叫添衣。
她真的在学校电视台播校园新闻时把自己的名字在屏幕上打成了添衣。
有个段子在我们那几届的很多人里一直流传,关于我们。
说是有一天,我这个平常不怎么上课的吊儿郎当,可能是听了传销课,不知怎么地突然想奋发图强,一大早就爬起来去第四教学楼上课,可惜我的一大早比一般人的一大早要晚了许多,还没走到便打了上课铃。我见时间来不及,就不走寻常路,直接从第四教学楼前学校花了大价钱引进的进口草坪上抄近路,结果被躲在四教大厅里蹲守的老师和校电视台逮了正着。老师授意添衣采访我,当时问了很多,答了也很多,但是晚上熄灯前在校园新闻里播出时却被掐头去尾。
添衣问,为什么从草坪走?草坪里有路吗?
我答: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
本来是批评教育的校园新闻,好像变成了哲学思辨意味的访谈。
那个晚上,听说很多寝室电视机前的学生们都敲起了桌子,许是好久没见过脸皮这么厚,面对指责批评满不在乎的人了吧,全校都传遍了,搞得好一段时间认识我的人都叫我迅哥。
段子里说我就是凭着鲁迅这句话泡到了添衣。
我承认确实踩了草坪也确实被抓了典型,而且的确说过那句话,但我绝没听过传销课,最重要的是添衣我早就认识了,不然我怎么会嬉皮笑脸地说这句话呢,本来就是在和添衣开玩笑。
我知道是谁在散布谣言,只能是李炜,段子肯定是李炜编的,没跑。那哥们和他女朋友叶馨是我们学校的校花校草,他们都是添衣在学校电视台里的同事,有一段时间我们四个人天天混在一起。
叶馨长得是真好看,李炜脸皮是真厚,我经常为之瞠目结舌,李炜当着当事人编起段子来都面不改色。他毕业后在市电视台汽车时代栏目里当主持人,说是主持人,其实是给汽车4S店做广告,作为车盲敢天天一本正经地在电视里点评汽车的也只有他了,叶馨后来去了市二台播天气预报。多年以后我曾回到那个城市和他们一起吃饭,他说叶馨抛弃他嫁给了诺基亚手机的一个总经销商,叶馨笑笑不说话,我笑笑不相信,十有八九是他放弃了叶馨娶了律师事务所主任的闺女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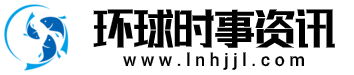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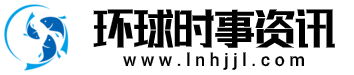
 主页 > 情感 >
主页 > 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