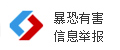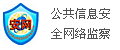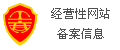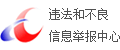|

1
我叫刘子周,今年35岁,重庆合川人,曾是一名货车司机。妻子陶丽比我小两岁,娘家就在嘉陵江对面。
都说男女一旦结了婚,生活就会越过越没味。而我俩人到中年,感情却浓烈得如初恋一样。但是,有一段时间里,我真的后悔死了当初和她的那场“艳遇”。
在我们那儿,货车都没有固定的客户。每天早上把车开到街上,然后约上三两个驾驶员,玩着扑克牌坐等客户上门。
我们称这叫摆地摊。
2010年3月12日,我和几个驾驶员正在车厢里打扑克牌,突然听到一个女孩的呼喊声:“抓贼!抓贼啊!站住!你别想跑!”
我循声望去,只见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孩气喘吁吁地追着一个年轻男子朝我们这边跑来。
我愣了两秒,立马知道了是怎么回事儿,连忙扔了牌,跳下车,在那男子跑到我面前的时候及时来了扫堂腿。男子被摔了个狗啃泥。
我冲上去,一只膝盖顶住男子的背,把他的双手掰过来。几个驾驶员也从车上跳了下来,大家一起把男子制服。
女孩儿追上来,照着男子的身子就是一脚。“狗东西!跑呀!干吗不跑了?”
我抓过被男子压在身下的黑色帆布包递给她:“先别忙打,看看东西丢了没有。”
她拉开拉链,抓出一个红色钱包,打开看了看,冲我笑笑:“没有,都在。谢谢你!”
有人打电话报了派出所。女孩说父亲被检查出直肠癌,马上要去县医院做手术。她刚回家凑了钱来,没想到居然碰到了摸包贼。
“谢谢你啊!我爸妈还在医院等我,我走了。”我让她等警察来了再走,到时候肯定还要当事人做笔录的。
她不耐烦地看了我一眼:“你不是人啊?没长嘴啊?”我被她呛得说不出话来,她却转身走了。
警察来了,我和几个驾驶员都结结巴巴,说不清楚事情经过。警察听得鼻子眉毛皱在了一起,说还得把当事人找来。
刚才听那女孩说她父亲要转院,于是我就把警察带到镇医院去。
女孩正在给父亲办转院手续。我连忙上前说明来意。她冲我吼:“这点儿事儿都说不清楚,你真是笨死了!”
她三两句就向警察说清楚了事情经过,说她还要送父亲去县医院,正忙着呢。警察迅速在本子上写了几行字,拿出印泥叫女孩盖手印。
她拿着一把单子要上楼,不耐烦地冲警察吼:“他话说不明白,盖个手印儿他也不会啊?”
警察说需要当事人盖手印。她才照做,盖完还生气地瞥了我一眼。
警察冲我直乐:“你们两个,可真有意思!”我双手一摊,真是又无奈又无语。
2
为这事儿,一起玩牌的几个驾驶员笑了我好久,我也气了好久。
本来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4月1日那天上午,我跑了一趟业务回来,刚摆好车,那个女孩又来了。“喂!我请你吃饭。”她一来就直接说。
我一愣,心里不禁暗暗叫苦。驾驶员小蔡打趣地说:“哦!子周,人家请你吃饭哦!”
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小蔡和其他几个驾驶员起哄:“喂,美女,我们也帮了忙的,干吗不请我们啊?”女孩说:“贼是他绊倒的,也是他抓的,又不是你们,干吗要请你们吃饭?”
遇上这种人,惹不起,我躲。趁几个驾驶员和她说话的机会,我赶紧打燃发动机,一脚油门踩回了家。
父母从屋里出来,莫名其妙地看看我,又看看货箱。我有些纳闷,刚想伸出头去看个究竟。头上突然像响起一声霹雳:“你这是开车?拿的飞行执照啊?”
我感觉天都要塌下来。倒是母亲高兴地迎上来打招呼:“幺妹儿,你……你是……怎么站在货厢里啊?”
女孩爽朗地一笑,一改刚才那又臭又硬的语气朝我父母鞠了个躬,说:“叔叔好!阿姨好!我叫陶丽,是专门来感谢他的。”
她指了指我。母亲一边埋怨我不让她坐副驾室,一边热情地伸手把她扶下来,还请她到屋里去坐。
陶丽把我帮她擒扒手、以及她父亲的事对我父母说了一遍。父母连声称赞她是个好女孩。
父亲去镇上买了些卤菜,又叫我到地里拔了一些青菜,挽留陶丽在家里吃午饭。
“本来是我请他吃饭的,反倒让你们请我。挺不好意思的。阿姨,那就让我来煮饭吧!”陶丽说着,硬是解了母亲的围裙自己系上。
一阵“叮叮当当”的锅碗瓢盆响,她还真做了一桌子菜出来。
3
陶丽走的时候,父母叮嘱她一定要经常来玩儿。
她答应了,三天两头往我家跑。她还见人就打招呼,有不认识的邻居问她是哪家的客,她就直接说我的名字。
这让我心里很烦,对母亲说别再叫陶丽来了,免得大家误会。母亲却说:“傻小子!人家是喜欢上你了,这都看不出来?”
母亲叫我好好待她。我把头摇成拨浪鼓,我说我可不找她,你们觉得她好你们自己要。
父亲一巴掌拍到我的后脑勺:“你个死孩子!都老大不小了,这么好的姑娘你不要,你要找仙女啊?”母亲捂住胸口哭:“哎呀!我这辈子是做了啥孽啊!你这孩子真的是要气死我!唉哟,我这胸口好痛!”
母亲一直心脏不好,受不得刺激,我也就只好妥协。好在陶丽那段时间说话没那么冲,特别是和我父母在一起的时候,还算得上很温和。
就这样,我们像许多农村青年一样,父母请了媒人到陶丽家里去提亲,然后双方父母见面,事情就基本上敲定了。
2010年10月1日,我和陶丽结了婚。2011年春节后,陶丽就怀孕了。
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好丈夫。尽管陶丽都怀孕了,我也还是没有一点儿要做父亲的准备。我天性大方,对人耿直义气。尽管打牌十赌九输,但只要弟兄伙喊,我几乎从不拒绝。
陶丽刚开始时还没什么,随着肚子一天天变大,她就变得越来越焦虑。特别是听说邻居家胎儿夭折的事,她更是坐不住了。
邻居媳妇检查出胎儿的胎位不正,本来该到大医院生产的,但因为没钱,不得不在镇医院生产,结果胎儿没出娘胎就夭折了。
陶丽对我说:“虽然我们孩子胎位正,不一定要到大医院生产,但一定要攒够去大医院的费用以防万一。”她叫我每天的运费全都要上交,由她统一保管。
我说我出门在外,钱放在我这里,遇上加油修车补轮胎的时候方便。她不同意,一定要我上交,说用钱的时候找她拿就是。
我生气了,说:“你又不是夜明珠,钱放在你身上难道就会多生出钱来?”陶丽不管这么多,我只要不从,她就又哭又闹又上吊,还拿肚子里的孩子威胁我。
父母也站在陶丽那边,说女人家女人家,女人才是一个家,所以钱就是该女人管。迫于压力,我只好乖乖就范。
4
2011年12月16日,陶丽在我们镇医院产下了儿子海川。
2012年春节过后,陶丽说现在多了一张嘴,用钱的地方多,她又不能出去打工,就在我家外面的路口开了个副食店。
原本以为,陶丽从此会把重心放到商店和儿子身上,努力做个贤妻良母。可我怎么也想不到,她反而成了一只随时可能发怒的母狮。
之前我每天出车,陶丽还给我点儿活动资金。可现在,修车加油都是她去结账,我身上被搜得比脸还干净。
她把商店分成里外两间屋,里面放了几桌麻将当茶馆,外面摆了货架做商店。过年了,人家都在斗地主打麻将,我却只能抱着海川站在旁边过眼瘾。
母亲实在看不下去,塞给我200块,说大过年的,玩两把过过瘾。陶丽回去就和母亲大吵一架,说我母亲是慈母多败儿。
她不但把母亲给我的200块和赢的几十块钱全部搜刮了去,还罚我煮了两天饭、洗了两天碗。大年初三,就把我撵了出去摆地摊。
身上没钱,我再不敢打牌了,也不敢出去吃饭。一个大男人活成这副窝囊样儿,我觉得特别没有面子。
我想到了藏私房钱。每跑一趟业务,我都会从中捞一点儿;一天跑的业务多了,我会少报两趟;有时候加油,我也会叫加油员在账上多写点儿,然后折合成现金给我。就这样,我又可以照样打牌喝酒了。
2013年3月的一天,我和几个驾驶员正在货厢里玩扑克。陶丽突然一骨碌爬上车厢,一把抓起扑克牌就撒了个天女散花。
“你妈心脏有病,你爸一大把年纪还在码头当搬运,你却在这儿装什么大鼻子象?”她愤怒地指着愣住的几个驾驶员说:“还有你们!没一个好东西!谁要再敢拖我家刘子周打牌,你看老娘我怎么收拾他!”
回到家,陶丽立马缴了我的身份证。说我既然攒私房钱,她就肯定要防备我办银行卡。没办法,我先后把钱藏在鞋垫下、内裤里、驾驶室的顶棚里,但都被她找了去。
最心痛的一次,是我好不容易攒起来的3000块钱,用废报纸包了藏在墙缝里,也被她打扫清洁给搜了去。
我想过把钱放在父母那里,可父母连连摆手,“算了,她那个性格我们可不敢惹。”
生活寡淡得像白开水,我像一台机器一样没心没肺地运转着。有时候,我真想出个轨。如果可能,离婚都可以。
2015年年底,我从镇上拉了一趟货去县城。正要返程,遇到了我初中时候的女神梁燕。她请我吃了顿饭,我们聊得相见恨晚。
我说我的生命中只有过去才是美好的,现在我就是一台挣钱机器,未来更不知道会变什么样子。
梁燕问我为什么这样悲观,我和她谈起和陶丽结婚以来的事儿。她说:“我能体会的,因为我就是一个不愿被约束的人,所以才离了婚。”
梁燕的这句话,让我在灰暗世界看到了一丝光亮。分别时,我们互留了电话和微信。每天,我都跟她聊得火热。
梁燕性格独立,自己在县城开着服装店。每次吃饭,她都争着掏钱。
我开始想象,如果我能和梁燕在一起,我们一定会互敬互爱,相濡以沫,一定会活成婚姻最幸福的模式。
5
我开始打小算盘,不再交运费,为以后离婚做准备。陶丽又拿出她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撒手锏,可已经在我面前不起作用。
2018年3月12日中午,陶丽说我在外面有人,要检查我的手机。我和她大吵了一架,开车就往镇上走。
车刚开出去五百米,我突然发现驾驶证没带。我连忙停下车,给陶丽打电话,得知驾驶证果真在家。我不想求她,就说了位置叫儿子给我送来。
我停在一个“Z”字型的长下坡,儿子经常和小伙伴一起在这玩。我停车打电话的时候,看到邻居张姨背着2岁多的孙子从下面上来。
经过我右边的副驾驶的时候,我滑下车窗和她打了个招呼。张姨背上的孩子是王小勇的,王小勇是我的同学,关系一直很好。
张姨刚走过一会儿,我从左面的后视镜里看到海川拿着我的皮包过来了。我一阵心痛,大人吵架,让这么个小孩子受连累。
我想让海川少跑一段路,就将车往后倒。车刚后退了几米,我突然感觉右后轮像是压到了什么东西。
我连忙刹车,往右后视镜一看,发现张姨躺在右后轮后面,她的孙子躺在离她两米远的地方。
我赶紧下车扶起张姨,又赶紧抱起孩子。见小孩口鼻流了很多血,我一边叫海川赶紧回家告诉他妈妈,一边火速把张姨祖孙俩送到镇医院。
“快,救救孩子!”我一手扶张姨,一手抱着孩子朝医生喊。医生见孩子口鼻的血还在流,赶紧清洗抢救。结果,孩子只是被碰出了鼻血和牙齿血。
我刚要松口气,张姨却突然倒地。我连忙和医生护士一起将张姨抬上推车。
经检查,张姨的腹腔、胸腔都在出血,内脏破裂。医生问我是不是家属,说因镇上医疗条件有限,医生建议我赶紧送县医院。
我这才想起给王小勇打电话,又报了警。王小勇在镇上开了家饭馆,接到电话赶紧跑过来。通过他微微战栗的身体,我能感受到他压抑的熊熊怒火。
“怎样了?检查过没有?”他努力让语气平和。我结结巴巴地说:“内……内脏……”“到底怎么了?”他突然瞪大了眼睛怒吼一声,红了的眼眶像要喷出火焰,分分钟要把我吞噬。
也许是他的声音太大,张姨被惊醒了。“小……小勇。”王小勇扑过去,“妈,你怎样了?哪儿痛啊?”
他握住母亲的手,拼命地想替母亲捂住伤口。可伤在内脏,他找不到,急得手足无措。
“妈……不行了。是他……压我两……”张姨话还没说完,突然头重重地一歪,那只被小勇握住的手慢慢瘫软下去。
“妈!”王小勇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我也双腿一软,朝张姨跪下。
王小勇颤抖着身子站起来,飞起一脚踢到我的脑袋上。我只觉得脑子“嗡”的一声,脸擦过一旁的金属铁架,头重重地撞在墙上。
“老子杀了你!”王小勇咆哮着朝我扑过来,医生护士连忙将他拉住。
一个护士赶紧拿来消毒棉给我脸上消毒,说我脸上出血了。我推开了她。比起心里的痛,脸上这点儿伤又算得上什么呢!
我真希望王小勇能够再踢我几脚,或者捅我几刀,这样我的心也会好受一点。
6
张姨就这样被推到了太平间。警察来了,我自觉罪孽深重,解下皮带、钱包和手机,随警察上了警车。
路上,警察说我这是交通事故,问我报保险公司没有。我摇摇头,我这车刚刚脱保才几天,怎么也想不到就出了这么大的事故。
警察说:“你这就事情大了。一条人命啊,怎么也要好几十万。”
我不想再说什么,钱都在陶丽手里。按她那性格和我们的状态,她绝对宁肯我坐牢,也不会拿几十万出来赔偿的。
到了派出所,我一下车,就看到陶丽抱着海川站在那里。她看到我,放下海川就冲了过来,说要把我抢回去。
几个警察把她拦住,说事情没有解决前,不能让我们有接触。
陶丽根本不管这些。她像一头发了狂的母兽,朝着警察又打又咬,披头散发地朝我这边冲。海川吓得“哇哇”直哭,大喊:“不要抓我爸爸,不要打我妈妈。”
一时间,现场乱成一团。
警察吓唬她,说她是严重阻碍执行公务,要把她抓起来。陶丽把头一扬,朝警察咆哮:“来啊!老娘死都不怕,今天谁敢关我男人,老娘就一头撞死在这墙上!”
放在以前,我肯定觉得这个泼妇不可理喻。可这次,我却想哭了!
身边的警察叫我赶紧阻止她,说她这样会把事情搞砸的。我这才回过神,对她说我没事儿,这只是解决事情所必需的过程。
警察也告诉她,我这只是交通事故,虽然死人了,但和其他犯罪是两码事。
陶丽这才平静下来,哭着问我:“他们说的是真的?”我朝她点点头。这么多年来,她第一次乖乖听了我的话,松开了抓着警察衣服的手。
在派出所做完笔录,警察把我带进一间拘留室。
里面空荡荡的,只有屋子中间放着一张木条椅。我主动伸出手,以为警察会把我铐起来。电视上,都是这么演的。
警察说不用,说我这是属于交通事故。但他也告诉我,从现在起,我不能离开这间屋子半步。
傍晚的时候,有人给我送了饭和一件军大衣。饭我没吃,军大衣我留下了。想着以后我就要在监狱里过,我说不出的难受。
夜晚,我用那件军大衣当被子,躺在长条椅上,满脑子都是下午那场事故的画面。
第二天又做笔录,我又把事情原原本本叙述了一遍。我一直等待着法律的制裁,可两天、三天……六天过去,做了那么多次笔录,却一直没有结果。
2018年3月28日,快中午的时候,一位警察来叫我出去。我以为又是要做笔录,干脆说:“算了吧,不做了。不管对我怎么处罚,我都接受。”
“怎么?还想在这儿待啊?自己回去了!”警察的话,让我如梦初醒。
回去,去哪里?刑场?我开始胡思乱想。跟着警察走出去,在一间办公室,警察让我在一份判决书上签字。上面写着我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期2年执行。
警察解释说,这叫监外执行,只要我这两年内不犯事儿,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了。当然,这2年之内不能离开居住地,并接受随时传唤。
在派出所门口,我看到了父母,他们牵着海川。还有陶丽!
几天不见,陶丽瘦了、黑了。看到我,她不顾一切地冲了过来,紧紧把我抱住。她把脸埋在我的脖子里,像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一样伤心地哭。
7
母亲告诉我,这些天,多亏了陶丽。
事故当天,陶丽跑出来看现场,但人已经送去医院了。她返回去拿了家里所有的钱,抱着海川赶到医院。那时我又被带到了派出所,于是他们又火速赶往了派出所。
知道陶丽是肇事司机的家属,派出所就让她和张姨的儿女一起协商解决此事。王小勇说他母亲临终的时候说我是故意压她两次,说我是故意杀人。
陶丽当然不信,她当着交警和张姨儿女们的面,扛了一袋水泥到车祸现场,让王小勇自己一遍遍地模拟车子在往上坡倒车时,压到障碍物踩刹车的情景。
最终得出结论:车子在往上坡倒车时压到障碍物踩刹车,由于地势和惯性的作用,轮胎会向前滚动一点微小的距离。
也许正因此,张姨感觉到我是来回压了她两次。又或许,张姨当时想说的“两”根本就不是压了她两次,而是压了她和孙子两个人。
王小勇控告我故意杀人的说法被推翻了。3月28日,法院主持双方就赔偿金额进行协商。张姨家属提出了40万赔偿金,说如果陶丽不同意他们就继续告。
陶丽一口答应,并当场取出了40万。
母亲说,为了求得张姨家人的原谅,办丧事那几天,陶丽每天都钉在张姨家帮忙。人家叫她给张姨当孝子,见人就下跪,见孩子也要磕头,她都一一照做。不仅如此,她还洗碗、扫地、搬东西,什么事儿都做。
有人替陶丽说话:“人家钱也赔了,该做的也做到了。车压到人谁也不愿意,差不多就行了。”
张姨的家人也不是不明事理,只是他们无法跨过张姨因我而去世的这个坎儿。
丧事办了整整7天。第6天晚上,陶丽实在太困,靠在张姨家的墙角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发现身上盖了件衣服。
第二天张姨出殡,王小勇就叫陶丽回去,说他会出具对我的谅解书,但毕竟他母亲是因我而死,所以想要再成朋友,这辈子不可能。
带着说不完的感激,我回了家。陶丽把电话还给我,说有个叫梁燕的女同学打电话来,知道我出了事儿,说如果经济上需要什么帮助,就对她说。
我以为陶丽向梁燕借钱了,因为我觉得,我们家不可能拿得出40万。
陶丽说:“我才不找她借钱呢!家里是没那么多,我把当闺女时存的钱拿出来,也就凑齐了。”我心头一阵心痛,拥她入怀。
我再也不跟梁艳联系了,甚至拉黑了她。一场风波,让我明白,大风大浪的日子,只有老婆能陪着我一起扛。
我被吊销了驾照,不能继续开车了。我在家里休息了两个月,陶丽也没再赶我出去找活儿干。
2018年6月8日,父亲帮我在码头找了个搬运的工作。因为这个活辛苦,很多搬运工都改了行,这样一来,我的业务并不少,挣的钱比我开车的时候还多。
我再也不藏钱了,每天回家就把钱全部上缴。陶丽也不再像以前一样把我搜刮得一分不剩,总是给我多留一些。说干搬运辛苦,饿了渴了就买点儿吃喝。
一个夏天过去,我被晒成了一块黑炭,看上去足足老了七八岁。晚上,陶丽摸着我被太阳晒得蜕了皮的肩膀,眼里泛起了泪光。
我不想泪眼婆娑,开玩笑地摸摸她的额头:“咋了?发烧了?也不烫啊!”她抱住我的腰,“如果我能多挣点儿钱,你和爸爸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2019年春节后,她在镇上盘了一家小超市。她让母亲去帮忙,早上卖早餐,下午卖卤菜。
晚上,父母回家后,我们一家三口就在超市的储物间里搭一张床睡觉。日子不富裕,我们却过得有滋有味。
2020年春节,一场疫情让很多人都光了家底儿。但我们,却商量着,如果房价跌了,我们就在镇上买一套房子。
两年的时间,我们手里已经攒了15万的存款,交一套房子的首付完全没问题。
都说好的夫妻是夫唱妇随,相濡以沫。但我知道,好的夫妻,其实是看对方陪你翻了几座山,趟了几条河。
我爱陶丽,我要跟她白头偕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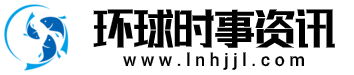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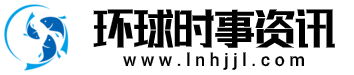
 主页 > 情感 >
主页 > 情感 >